时间:2023-04-12 15:22:00
年鉴学派作为20世纪著名史学流派,把史学研究的新观念引入历史研究领域,构成了年鉴学派史学范式的本质特征—总体史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年鉴学派在历史研究中所倡导的问题史学和由古至今、由今知古的治史方法,可以为党史研究提供更广泛和更科学的依据,促进党史研究在角度和深度上的进一步拓展与提高。
年鉴学派是20世纪国际史学界最著名史学流派之一,是法国自1929年以来主持、编纂《经济与社会史年鉴》的几代历史学家共同创立的。这些历史学家把总体史和跨学科研究的新观念和新方法引人历史研究领域。他们的理论不仅震撼了法国的史学界,而且深刻影响了整个现代西方史学的发展。就其影响而言,“年鉴学派已比任何的史学流派都更胜一筹,成为今天全世界历史学家进行科学性历史研究的典范。”①年鉴学派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系统地被介绍到中国,始于张芝联先生在《法国史通讯》1978年第1期上发表的《年鉴学派简介》一文。此后,对年鉴学派进行探讨的文章层出不穷,而且作为一种研究范式被广泛地应用,党史研究完全可以汲取其中的思想,向更广更深的领域发展。
一、年鉴学派主要的思想观点分析
1900年贝尔创办的《历史综合杂志》,它反对传统的记叙史,倡导对历史进行理论研究,认为历史学的任务是解释历史,而不是描述历史,要进行综合的研究。这一宗旨为年鉴学派的创立及跨学科研究开了先河。年鉴学派经历了从年鉴学派到年鉴·新史学派的历程,基本上可分为三个阶段:初创阶段(1929-1946 ),代表人物是费弗尔和布洛赫;鼎盛阶段(1946-1969),代表人物是布罗代尔;新史学阶段(1969一今),代表人物是勒高夫等。总体史研究和跨学科研究,这两大特点构成了年鉴史学范式的本质特征,贯穿于年鉴学派的整个发展过程中,成为一条红线。
1.开创总体史,反对历史局限于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的领域。作为年鉴学派的创始人—费弗尔开辟了总体史的道路,认为总体史包括了整个人类的生活,历史是人的科学,是研究人的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历史,提倡多学科综合研究方法,坚持历史无界限。在年鉴学派的思想中,“历史研究不容划地为牢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②其次,否定历史研究中的“政治偶像”。反对政治史在史学中的统治地位,尤其是外交政治史。认为“政治史一方面是一种叙述性的历史,另一方面又是一种由各种事件拼凑而成的历史,这种事件性的历史只能是掩盖了真正历史活动的表面现象;而真正的历史活动则产生于这些现象的背后,产生于一系列的深层结构。”③基于这一认识,费弗尔在《马丁路德:一个命运》中研究了16世纪德国社会的精神风貌和集体心理,开创了法国心理历史学的研究。
2.推行群众主义,否定个人偶像。年鉴学派反对政治史、军事史的主导地位,注重社会史、精神状态史等研究。强调历史非个人历史,研究不能只围绕人物,而不围绕社会制度、社会现象或种种联系去思考。尤其反对在历史研究中只注重大人物的历史,“除显要人物的历史外也应给小百姓历史一个地位;在一个遗传继承的社会行为系统之中和一个表面上持久不变的空间环境之内出现过一些诸如改良过采伐技术的一个普通农民,他们是和赢得了一次战役的将军具有同等重要性的历史人物。”④这种思想使历史的研究由上而下移,使研究材料的来源更加丰富。“草根”阶层在历史研究中地位的提高,是扩大历史研究范围、增强历史真实性的重要因素。
3.历史时段理论。1946年,《年鉴》杂志改名为《经济、社会、文明年鉴》,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提出了历史长时段理论,从理论上阐述了不同层次的历史时间在总体史研究中的意义,强调历史事件具有不同的节奏和多元性。他把历史时间分为“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各自解释为:结构或自然时间,是长期不变的缓慢现象,如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社会组织、思想传统等等;局势或社会时间,是在一定时期内发生变化形成一定周期和结构的现象,如人口的消长、物价的升降、生产的增减;事件或政治时间,主要是历史上突发的现象,如革命、战争、地震等等。这三者在历史中所起的作用是:短时段转瞬即逝,对整个历史进程只起微小的作用;中时段现象对历史进程起着直接和重要的作用;只有长时段现象才构成历史的深层结构,构成整个历史发展的基础,对历史进程起着决定性和根本的作用。因此,年鉴学派认为历史学家只有借助长时段的观点,研究长时段的历史现象,才能从根本上把握历史的总体。这一理论冲击了传统史学狭隘的政治史观,进一步体现了年鉴学派总体历史学的思想。
4.向局部历史、微观历史的转变。年鉴学派发展到第三阶段,被称为新史学。年鉴史学向局部历史、微观历史转变,注重数量分析方法。传统的年鉴学派提倡总体史学,把社会看成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而第三代学者却强调历史的间断性是决定一切的因素,否认各种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性。他们对其宗师提出质疑:“总体史显然是没有意义的,它是一种愿望,标志着一个方向”。因此,这一阶段注重研究一些历史上孤立的现象或细小的课题。如《气候:晴雨史》、《身体:病人和他历史》等。同时,传统的政治史和人物史也开始复兴。这一时期历史人类学研究得到重视,精神形态史也有了进一步发展。现今的年鉴·新史学派的理论、方法和研究领域缺乏一种统一的精神,在某种意义上已不是一个学派,而是一个运动。
二、年鉴学派在历史研究中的方法论应用
年鉴学派在发展中既有史学思想的凝结,又有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启示,《历史学家的技艺》、《历史学家的领域》、《在历史学家中间》等著作给历史学家研究历史提供了基本的方法论,也可以为党史研究提供借鉴的治史原则。
1.由古知今、由今知古的历史研究法。布洛赫认为要了解现实就必须超越现实,要探讨历史亦不可囿于历史。史学家探究历史必须从古代中发现与现实相联的因素,密芝勒在《人民》开篇中说:谁把思想局限于现在,谁就不能了解当今的现实。因而历史研究必须从古至今。但同时要抵制“起源的迷惑”。布洛赫打破了以往史学家站在遥远的过去来解释当前,从起源揭示事物本质的“起源偶像”。在他看来,“任何研究工作,其自然步骤往往是由已知推向未知的”⑤。因而,在进行总体史研究时推行倒溯复原的方法,从“明晰”到“模糊”,即“历史学家为了重构已消逝的景象,就必须从已知景象人手,由今及古的伸出掘土的‘铲子’。”⑥由于缺乏文献记录等原因,史学家对一些历史的认识往往是模糊的、有限的,为了阐明历史,往往将研究课题与现实挂钩。通过现状去研究历史整个发展过程,这是历史学家研究的重要方法。党史研究是历史与现实、过去与现在的结合体,在史论结合的基础上承上启下。在研究历史中的单一事件或运动时,越来越多关注其对现今中国发展的影响;在研究整个发展史时不仅结合时间先后顺序,在现实中寻找根源,在历史中探索经验,同时采取回忆录、口述的方式来研究和记叙。这其中包括政治高层人物,也包括有亲身经历的各种人物,正确运用这些方法和资料是党史研究全面系统的关键。
2.问题史学是年鉴学派的重要的方法论原则。问题史学是“不是一种让史料自己说话,而是由史学家提出问题的史学。”⑦历史事实并不等于已知条件,它只是史学家从历史文献资料出发构建而成的,这就是所谓“存疑”的历史观。问题史学要求提出假设,提出要解决的问题,然后搜集和分析史料,证明假说成立与否,最后解决问题,找出历史过程的逻辑。费弗尔说:“提出一个问题,确切地说来,是所有史学研究的开端和终结。没有问题,便没有史学。”⑧因而,这一方法论使历史研究从“文献历史”和“事件历史”的单一框架中摆脱出来。对历史不仅仅是叙述和重视,也不能局限于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重要的是对历史的分析和解释,否则,历史学会趋于狭隘和肤浅。这一方法论打破了以往研究回复历史真面貌的目的,年鉴学派成员的研究目的是“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视从现时出发来探讨历史问题,以便能在一个‘动荡不宁的世界中’生活和理解”⑨。史学家总是怀着明确的目的,从现实出发去研究历史。许多课题的构建是在现实中挖掘,在历史中分析和解释,启迪人们更深刻地认识现实社会。
三、年鉴学派思想理论对党史研究的启示
1.党史研究须从总体上把握,注重宏观和微观的结合,不论是撰写综合史还是专门史或微观史。历史是政治、经济、文化等系统构成的人类社会活动的总体史或综合史。党史研究初期更多的从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的领域上去研究,使党史研究处于一个很有限的领域内,胡乔木的《中国的三十年》、王实等的《中国历史简编》、胡华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初稿)这些是党史研究的重要成果,但都从政治因素出发论史,使研究限于政治史的框架之中。后来胡绳的《七十年》和沙健孙的《中国通史》则摒弃了单纯从政治因素论史,对党史进行了较为全面深人的总结,在资料和史实上日渐详实。同时在对某一问题的分析和论断上越来越从细微处着手,注意微观史研究的全面性。党史研究应注重从细微的、局部的或专门的历史中去探求,这些历史使我们的研究趋向细化,为整体史的研究提供重要的、全面的资料。但在对微观史的研究中既要全面细致,又要在宏观上把关,应把它放到党史研究的整体框架中去考察,放到整体历史背景与发展进程中去思索。
2.党史研究要突破学科限制,注意研究的多元化。跨学科研究是年鉴学派的基本治史方法。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研究的深人,党史研究也应突破以前的学科限制,应当与其他学科相结合。党史发展中的事件以及问题是社会中诸多原因的多元化的整合,利用跨学科可以使党史研究在深度上更深人,范围上更拓宽;从多维的角度去思考,不再囿于政治、军事、文化领域,而应当融合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民族学、地理学甚至是图书馆学、新闻学等学科,对社会史、心态史、民族史等进行研究。这样的方法能使党史研究的角度不断更新,而且分析问题更加全面、系统。例如当代社会问题及对策研究已成为党史研究的新领域和新方向。张静如教授在继《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和《国民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之后于2004年主编的《中国现代社会史》,从经济与政治、教育与文化、阶级与阶层、社会组织、家庭、社会习俗、社会意识等方面展开对中国现代社会发展历程的研究,是近年来社会史研究方面的一部力作。从社会史的角度出发研究党史,可为党史研究提供全新的视角。
3.党史研究要重分析和解释,注重现实意义,采用问题史学的方法论原则。年鉴学派要求对史实不是单纯采取实证态度,而是科学地收集资料,通过分析资料重建和解释过去,研究历史的可借鉴因素,体现其研究的价值和意义。问题史学的方法论的应用可使党史研究更加深入和理性。随着社会和实践的发展,党史研究的方向在不断地更新,基于对现实思想或政策、制度的思考,党史研究应从多角度进行分析;再者与现实紧密结合,探索有价值的课题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地。如中国与中国现代化,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党建研究等等。从现代化这一角度透视党史研究,可以从宏观上把握党史进程,也可从微观上挖掘党史上的某些革命运动与现代化的关系,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都具有现实意义。
4.注重历史时段理论的应用,将历史进程中“长时段”和“短时段”结合起来研究,探索新的全面的史学研究领域。“对于一个当代的时期(只要确定它的起点就够了),人们看到的是历史的运动性,是寓于各种事件中的历史的冲动性;而对于一系列以前的时代,人们看到的是历史的不动性和历史缓慢前进的长时段。”⑩“长时段”和“短时段”是历史发展的共同因素。年鉴学派的“长时段”理论对改变党史研究方式具有这样的应用价值:第一,从社会运动到社会结构的研究。党史研究不应再仅仅局限于对社会运动的探究,而应注意从促进社会发展的整体结构方面去考察。第二,把心态的研究作为一个重要领域。米歇尔·伏维尔把心态作为长时段的优势领域,心态是社会的稳定因素,反映历史运动和社会进程,这方面也应是党史研究的重要方向和重要课题。年鉴学派坚持长时段理论,却忽视“短时段”在历史中的作用,“短时段”尤其是一些有转折意义的运动对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同样起着关键的作用,譬如党史上的五四运动、工农红军长征、抗日战争、十一届三中全会等等。党史研究必须摒弃年鉴学派理论的局限性,重视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的研究,将“长时段”和“短时段”理论紧密结合起来,推进党史研究全面和深入地发展。
免责声明以上文章内容均来源于其他网络渠道,仅供欣赏,不代表本站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仅供学习和参考。如有涉及到您的权益,请来信告知(email:mlunwen@163.com),我们核实后会立刻删除。

4区
Bimonthly

3区
Bimonthly

Transportmetrica B-transport Dynamics
3区
1 issue/yea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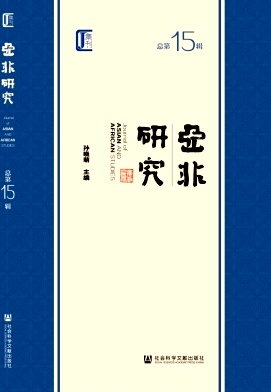
部级期刊
半年刊

省级期刊
双月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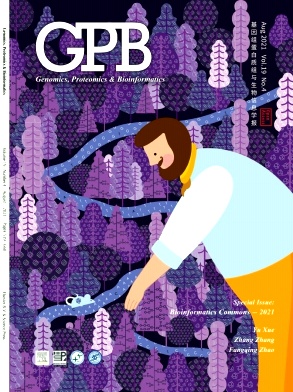
SCI期刊
双月刊

Journal Of Noncommutative Geometry
4区
Quarterl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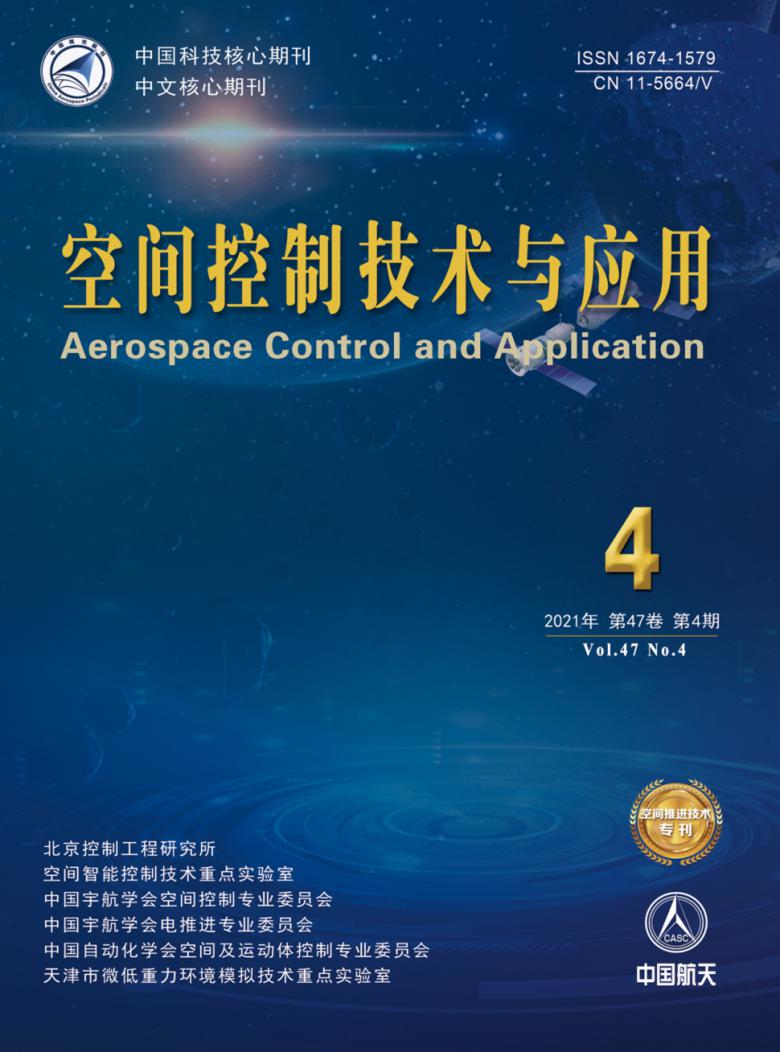
CSCD期刊
双月刊